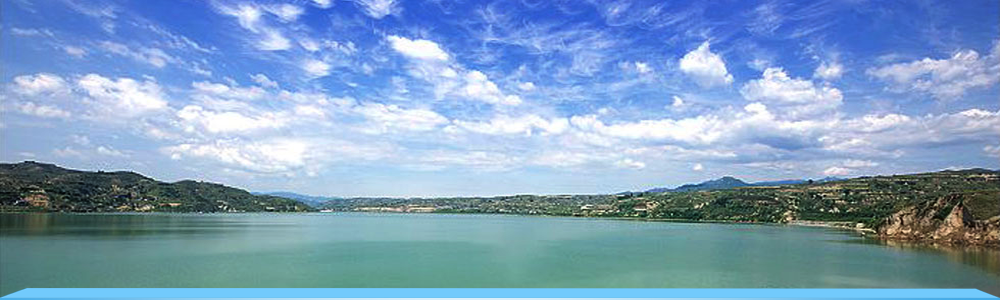我之所以要写一写雷苹,全是由于她和我都吃过我母亲的奶。
(一)到雷苹家吃饭
1976年暑假,母亲带我从农村到县城里来,那时我六虚岁。我家在农村,第一次到城里来,经历了许多从未经历的事情,而雷苹的母亲请我的母亲和我到她家吃饭,就是我从未经历的事。
一大早,母亲梳洗要比往常仔细些,这是我在玩耍间捎带知晓的,但我并不知晓这是将要发生的一件盛事的开头。
母亲快梳洗完毕时,雷苹来了。她来请母亲和我到她们家去吃饭。雷苹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端庄,黑亮而重的头发扎两根半长的辫子在肩上,眼睛花而大,周正的五官配着喜气的大脸盘和她不低不瘦的身材。可我之前没有见过她。她见了我的母亲竟非常的亲,仿佛以前就亲过似的。雷苹来了之后,就和母亲说着话。母亲边梳洗收拾着。母亲是个利索的人,何况她的女儿已经来请她了呢,何况她自己也着急着想去了呢!不一会,雷苹便牵了我挽着母亲出了门。
雷苹母亲的家在县城南门外河对岸的东峁村,从父亲单位起身,走出河渠街,不到水门便向南拐,再沿街走出南门外,朝东过了大桥便是,约摸三几里地吧。一路上,雷苹挽着母亲说着话,走着,倒像是一对母女;我则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的游散而相随着,没多久也就到了。
雷苹母亲的家在东峁村的尽西头,过了桥,走一段斜而陡的坡,上得一处巨大的沙岩石盘上便是。一所农村小院,进了小小的大门,正面三孔石窑,雷苹母亲的家是西边的一孔窑洞。窑院的西侧是一段断砖墙,低低的,以至于六岁的我,刚进了窑洞又出来的时候,便发觉从这儿可以瞭得到公路、大桥、河柳及刚才走过的湫水河。院子里没什么人,似乎有小石床、板凳和一些杂物,有小小的莱畦栽种些菜蔬,有明亮的阳光和阳光投下夏日的荫凉。我便来来回回的在其间玩,直到雷苹出来牵我吃饭。
雷苹的母亲请我们吃的是拉面。虽然我来到世界上已经一千五百多个日子,但所见过和吃过的白面也没几回,这其中拉面应该更少甚或究竟吃过没有?只有白面才有的白的拉面卧在干净的碗里,冒着热气、发散着只有筋道的白面煮熟后才有的泽光,飘散着麦面的香。用来调面的调料有很多:盐、葱、醋和芝麻面是常见的,芫荽、韭菜、黑酱却很稀奇,而旁边更有一碗我未曾吃过的油炝西红柿酱,也未见过的——那时我们村还没有西红柿栽种。母亲告诉我这是柿子,雷苹母女则称之为西番柿,这大概是习语的不同吧。于是,因了这一碗西红柿酱的缘故,这顿客饭的名字便叫做“柿子面”,这也是她们告诉我的。筋道的小拉面,丰盛的调料,更加上油合西红柿酱养眼鲜艳的颜色、独有好吃的滋味,这是我一生以来所吃的第一顿最好吃的饭了!
1976年距今四十多年了,我还常记起那碗面。或许就是在饭间吧,我知道了,雷苹的母亲是母亲的朋友,她之所以请母亲和我到家里吃饭,是因为母亲到城里来了,她要表达朋友间的情谊。雷苹的母亲是一个白而羸弱的妇人,因为白,显小,又因为弱,显老,所以综合下来也许就是她实际年龄的样子,约摸不到四十岁。大眼睛,干净,安静,脸上有弱的笑意。
或许在饭后,我就睡了吧,那天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
(二)雷苹的“父亲”
再后来,听母亲说,为了谋活法,雷苹的母亲现在跟一个叫雷师的人一起过,因而雷苹也就姓了雷。她们在东峁村租了窑洞来住。雷师是县里国营照像馆的照像师,因为照像技术最好,人们就都称他为雷师。那次雷苹的母亲请我们到家吃饭时,雷师因为上班,所以没见到。雷师本是晋中地区平遥县人。1971年,吕梁地区从晋中分出来,雷师就被分来我们县工作了。雷师在老家有孩子,但没有了女人。雷苹的母亲跟雷师结合的时候,谈好了条件,雷苹随雷师姓,但是将来雷师退休的时候是要由雷苹来顶班,雷师也同意。说起来,雷苹的母亲能跟雷师结合还是因为两人的老家一个是文水,一个是平遥,是紧相邻的两个县,又因为一个是“右派”遗属,一个成份高,又都落在我们县里的缘故呢。母亲说,雷苹的生父姓张,是个大学生,是个工程师,本来在老家文水县工作,因为是“右派”,被下放到我们村子的学校教书。风闻,张老师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本来是不够“右派”资格的,只是当时他们老家县里知识分子太少,而张老师又是大学毕业,所以就把他弄成“右派”了。所以,张老师才来到我们这个黄河边上穷苦偏远的小山村。张老师身体不好,村里人认为,他是读书太多以及从平川的城里来到这瞎坡烂窊的山村里水土不服造成的。
张老师没有结婚,可是谁问给他呢?张老师是文化人,虽则是“右派”,但也是有工作的人,有文化有工作的姑娘,村子里没有;没文化的姑娘,觉得张老师看不上,觉得一跟张老师就成“右派”家属,也是不行的。因而,张老师在我们村教书的前几年,是身体不好而未婚的。
但有一年的麦假起来,张老师从老家回到我们村里复课的时候,却带来了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雷苹母亲。他们在我们村里安了家,和我们家就在一道圪堎上。那时,我们村里人都怪怪的认为张老师的妻子来路不明似的,但母亲说,她是知道的,张老师再怎么也是文化有工作挣工资的,虽说是“右派”,找不下条件相当的,却总不至于连个婚也结不了吧。其实,张老师的妻子还是张老师在麦假里回了老家挑的呢!张老师的妻子虽没工作,但是有初中文化,模样也颇周致俊俏,人家是正式结婚的呢。
(三)雷苹母亲和我母亲关系很好
母亲说,那时,因为“六二压”的原因,张老师的妻子没了工作,户口也转成了农户,正好带着两个孩子,从城里回到村子里安了家。就是因为这样两个机缘,雷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成为了朋友。母亲时常帮衬她们,她们的关系越来越好。
当雷苹母亲生下雷苹的时候,她和我母亲的关系就更好了。雷苹母亲没有奶水,而母亲呢,当时正奶着她的第三个孩子,奶水足的很,便捎带着也奶上了雷苹。这种奶呢,只是雷苹母亲大部分时间抱了雷苹在我家玩耍和让雷苹吃母亲的奶。因为是不收钱的,所以也无需让雷苹认母亲做奶妈。母亲说,虽则在“六二压”以前,工作很忙,她两个大一些的孩子都是花钱找了奶妈,但她之所以奶雷苹,却是因为雷苹母亲身子弱、没有奶,雷苹母亲是她的朋友,所以是不收钱的,所以也不能让雷苹认她做奶妈。母亲说,本来是不收钱捎带着奶的,但如果让雷苹认了妈,将来就会给雷苹落下亏欠,是没用的。但她却真是把雷苹当作女儿看待。由此,雷苹母亲和母亲的关系就更亲了。
母亲捎带着奶雷苹有一年多吧,雷苹的生父就去世了。雷苹母亲只好带着雷苹离开了我们村子。1976年夏天,当雷苹的母亲请母亲和我吃柿子面时,那是母亲和雷苹母女分开后的第一次相见。
母亲说这些不是一次说的,是后来的多少年里说到雷苹的时候陆续说的,而我,也是陆续听到的。
(四)我终于见到了雷师
1980年,国家落实“六二压”政策,母亲和她六二年以后生的孩子“农转非”后,举家又迁入县城里了。那时,我十岁。
不久,雷苹就来家里看我们,还给母亲带了礼,给我带些零食。雷苹是骑着雷师给买的自行车来的,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头发仍黑亮而重,个子更高了,依然不瘦,脸红扑扑的,热气腾腾,见了母亲像女儿似的,依然亲。雷苹已经高中毕业,现在跟着雷师在国营照像馆当学徒,不算是正式工,但须正规地去上班。她让我叫她姐姐,让我到照像馆找她玩。
这次我来到城里后是定居,学也转到城里来上了。虽然1976年第一次来城里到过的地方还有些记得,但更多的却是新奇的天地,更何况十岁的人要比六岁的人不知厉害上多少倍!那时,上学完了,我便是没边没沿的疯跑。国营照像馆就在父亲单位跟前,又因为雷苹在这儿上班,因此便成了我疯跑期间经常落脚的地方。那时,照像馆是一种严肃、神秘的地方。全县仅此一家,还在二层楼上;照像室是一间黑屋子,全靠灯来照亮;暗室则更是可怕的所在,外人绝不进出;照像师技术莫测,推着蒙了黑布的像机移动着,捏得一个气囊扑哧扑哧的响,如此,便感觉照像师也是神秘的人。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雷师。他是这里的首席照像师,人清瘦而刻板,操外地口音,话很少且不易懂。徒弟们也很少说话,整个照像馆内是一种寂静压抑的气氛。这样的地方使我在第一次跟雷苹去过之后便不欲再去。然而,情形发生了变化,和雷苹一起学徒的临时工,是一个十七岁的大男孩,竟然和我家住在一个宿舍院子里,他活泼淘气,很快就与我淘到一块去了,因为他常常偷偷叫我去,才使我在后来又去照相馆多了起来。雷苹待我很好,水自然是常备着让我喝的,偶尔还有糖果、瓜子之类的零食。我是从来不喜零食的,但我晓得这是雷苹对我的好。雷苹和大男孩同在一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成天拿了2B的铅笔来修黑白胶卷的底片,我去那儿,有几次见到雷师去教她们,因为小学生写字用的也是铅笔,我便硬要感觉这情景正与我们班上的老师教那些不会做功课的同学一般。雷师看到我也很少说话,但感觉他对我还好,至少从来没有撵我走过——的确有几次我见过他把周边单位其他人家的孩子撵走的。我想这是为了雷苹的缘故吧?在照像馆,我偶尔还碰到雷苹母亲几次,不知是来找雷苹,还是来找雷师的。
(五)雷苹走了……
雷苹还是间或来我们家走串,有时带几个饼子,有时带着点水果,有时带些菜蔬,来了之后,就主要是和母亲说话,很亲。一次,在我进进出出的玩耍间捎带听见她们在闲聊顶班的事,但我没有听全。然而,这则讯息,在当天晚饭的时候,我就从母亲给父亲的转述中,得知了全部。雷师要退休了,准备给雷苹办顶班,非农户口、高中毕业、父女关系,这些条件雷苹是都具备的,所担心的,一个是怕有人找茬挑剔他们的父女关系;另一个是怕领导们暗地里使办法把雷师的这个指标给占了去……
雷苹的顶班没出现那两种担心的困难。一年后,顺利地转正定级了。我在上学及玩耍之余有时仍然会去照像馆落落脚,但因日渐长大玩的更野,以及雷师走后他原来的大徒弟管的更严的缘由,竟至去的少了。雷师退休后回了平遥,据说,雷苹母亲起初也是跟了去的,可不久,因为和雷师的孩子们无法相处,踅返回来又跟着雷苹了。
秋天的一日,雷苹下班后,骑自行车到家来看母亲,照例很亲地和母亲说话。这次来,雷苹带着一包喜糖,雷苹跟母亲说,前几天她回文水老家订婚了,对象也是文水人,正式工,家庭和人都还行,是老家的亲戚们张罗着给介绍的。雷苹说,已经定下了婚期,八月里结婚,到时也请母亲一定要去文水参加婚礼。雷苹说,男方提的要求是结婚后雷苹须调回文水工作,那边已经说好有一个国营单位接收,只是担心这边单位不放人。雷苹的脸上本来洋着喜色,但说到这一担心的时候,露出了一丝的难意。母亲安抚她说,这不会吧。
雷苹的婚礼母亲到底还是没能去成,但随了礼,是一块做衣服的料子和十块礼钱。雷苹顺利地调回了文水。刚开始几年,母亲还会偶尔惦记起她来,但再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电话还不普遍,所以也没有联系。再后来,母亲也就很少说到她了。
只是我,在记及和说及那碗一生中最好吃的柿子面的时候,还是要想起这和雷苹相关的一些事。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
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